
走出舒適,忘掉安全。生活在你所恐懼的地方。毀掉你的名聲。做一個惡名昭彰的人。 — — 魯米
艾德烈·洛爾德在她與癌症搏鬥的八零年代裡,主張照顧自己是一種政治鬥爭。自此,自我照顧就成為行動者圈子間的熱門詞。現今人們談論自我照顧這個概念時,其內容已由當初指向具體情況,變為指向人們生活的所有面向;而當初充滿反抗性的說法,亦已變為戒律般的言辭。當今天我們談及自我照顧時,我們還是跟洛爾德在講同一樣的事情嗎?今天讓我們來審視一下這個概念。
但是 照顧 有甚麼可能會出錯?而且為甚麼偏偏要談論「自我照顧」?

首先,它已變成神聖不可挑戰的概念。要聽人們偽善地發表偉論,尤其在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上,是十分痛苦的。道貌岸然的一致性就表示著黑暗面的存在:正如不公義亦藏身於每間教會的陰影底下。自我照顧的概念製造了「他者」,也在我們自身之間劃了界線。
自我與照顧 — 自我總被放置先於照顧,而這樣的次序卻是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提倡自我照顧的人都是「道德完善」的一方,也即是說,否定所有我們身上與現存價值系統無法相容的部分。若我們要反抗這主流的秩序,我們需要唱反調,尋找所有被排除及被抵毀的事物。
每當有一種觀念變得理所當然的時候,我們就會見到它作為規範所生產出來的壓力:例如要為了他人而操演照顧自己的壓力、時刻保持外觀得宜的壓力。我們努力在社會中維持一個成功的、獨立個體的形象,即使它與現實相違。在這個語境下,自我照顧的說辭就掩蓋了打壓及控制的過程:你應當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拜托,不然就有人要處理你的鳥事。
認為自我照顧必然是正面的,其實是假定了「自我」和「照顧」有著永恆地不變的意思。在此,我們希望挑戰兩詞固有的僵化、鐵板一塊的理解。我們提出,不同的照顧會生成出不同的自我,而照顧就是社會革命其中一個戰場。
別叫我冷靜下來
儘管主張自我照顧的人常說方法是因人而異,但他們的建議卻常常可疑地相似。當說及最典型「照顧自己」的活動時,你會想到甚麼?喝一杯花茶、看電影、泡泡浴、冥想、瑜伽?這些選項對於何為自我照顧只描繪出一個很狹隘的畫面,基本上它們所提議的是,讓你自己冷靜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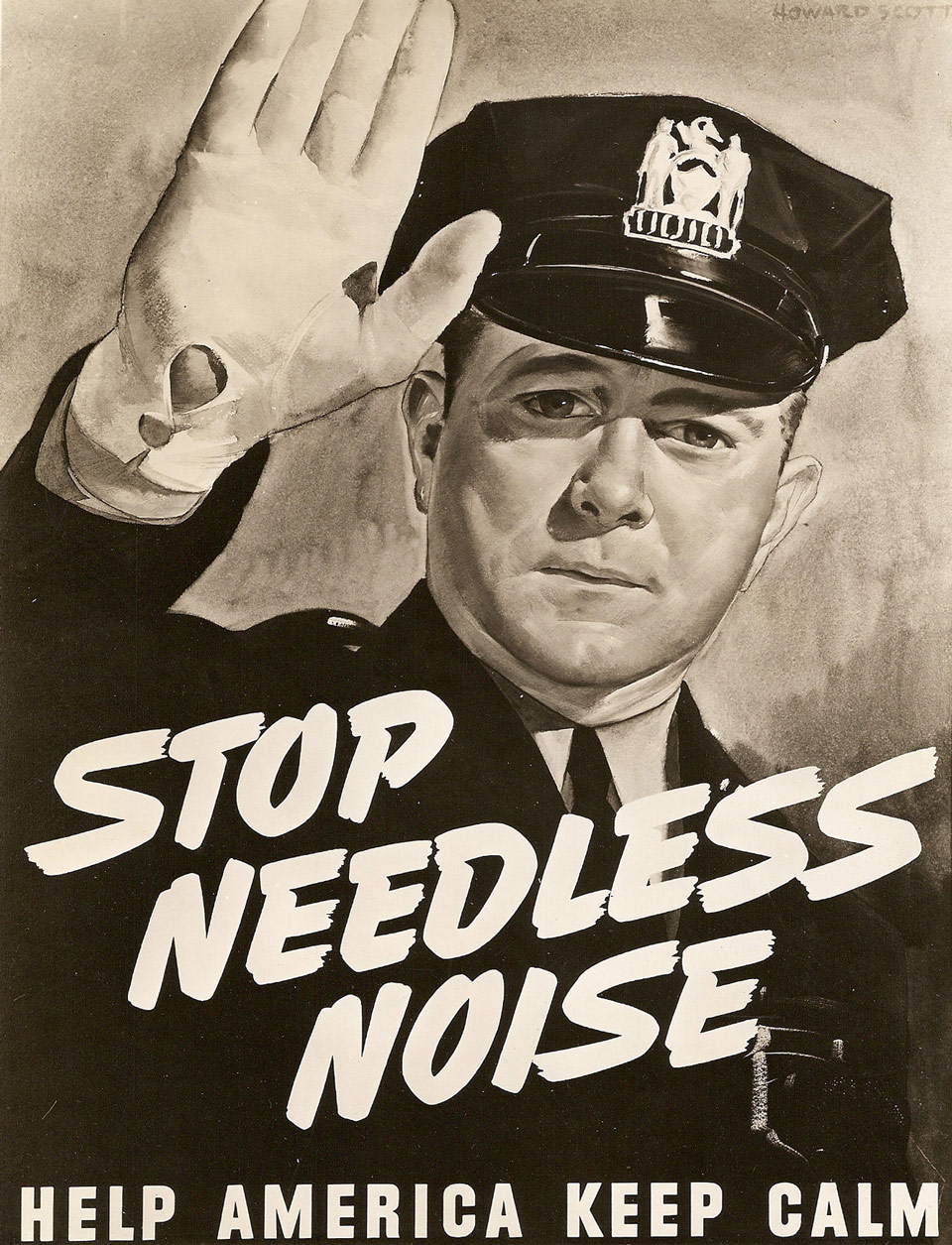
所有這些活動都是為了啟動負責休息及復原的副交感神經系統,但有一些照顧的方法是要進行劇烈的活動,以刺激屬於交感神經系統區域的腎上腺素。其中一個防止創傷後遺症的方法是,舉個例子,容許交感神經系統有足夠的自由去釋放身體的創傷。當一個人恐慌感來襲時,嘗試讓他們冷靜下來往往都沒有用。最好處理的方法是跑步。
讓我們先拋棄一般「自我照顧」的想像吧。它可以是指點起蠟燭,播放妮娜·西蒙的CD,重讀藍道·哈瑞爾的《動物家庭》。它也可以是指皮繩愉虐(BDSM),激烈的行為藝術,總合武術,打爆銀行的玻璃窗,或指罵一個曾虐待你的人。自我照顧,可以是做旁人看來似是苦活的活動 — — 或是旁人會覺得完全沒有作用的活動。這並非後現代主義「各施其法」、「各有所好」之類的陳詞濫調;而是我們要與自身所面對的挑戰和痛苦建立一個怎樣的關係。
照顧自己不等於要鎮靜自己。我們應對所有將平靜等同心理健康,或要求我們為了別人而要變得健康的說法抱有懷疑。我們可以想像這樣的一種照顧形式嗎? — — 能讓我們更好地去與陰暗面建立一種有意識的關係,讓我們能從混亂的漩渦中抽取力量。對自己溫柔可能是其中必要的一部分,但我們必不能假定「治癒」與「面對身邊及內在的挑戰」之間是分離的關係,兩者可以是同一回事。如果只是為了逃避問題而進行那些所謂照顧自己的活動,我們就會永遠來回拉扯於逃離後的不滿足感,及問題繼續伸延的負面後果之間。
這一種照顧不是用陳腔濫調可描述得到的。它不是一個可以輕易加到一般非牟利組織的項目。它需要我們擾亂現時社會的崗位角色,把我們帶到社會層面的衝突之中,甚至要挑戰那些聲稱正在嘗試作出改變的人們。
「從你對危險的反應可以反映出你一直是如何生活的,以及你的遭遇。這些反應透露了你是否希望繼續生存,你是否認為自己值得生存,以及是否相信作出行動是善的。」 — — 珍妮・侯哲爾
愛就是戰場
如果我們想要分辨在照顧裡面有甚麼是值得保存,我們可以先仔細觀察照顧本身意味著甚麼。若認同照顧是一種普遍的善,就是忽略了照顧如何在延續及惡化現狀 — — 最差的那一方面。世上沒有一種純粹的照顧 — — 照顧不能從資本主義的日常生活及反抗之的抗爭中抽空出來談論。照顧是一體兩面:壓迫或解放的。有某類型的照顧是複製了現有的秩序及邏輯,亦有是可以裝備我們去反抗的。我們希望我們提出的照顧可培育解放的土壤, 以一種不同的邏輯和價值把人們帶在一起,而非統治和控制。

從家務勞動至專業的家務工 — — 還有護理,服務業以及性工作,女人和有色人種不合比例地負上照顧者的責任,讓社會得以繼續運作,然而她們卻在其中有著不合比例地少的發言權。同樣地,大量這些照顧的成果成為了延續這個不公平層級現象的燃料:警察下班後家庭提供了放鬆的場所,性工作者幫助商人減壓,管理層人員的婚姻也是靠著秘書們默默工作才得以維持。
所以關於自我照顧的問題不單是其個人主義式的前設。對我們某些人來說,對比起照顧他人,能夠專注在自我照顧已算是革命性的,儘管這已經夠難想像。當一些人可以誇耀自己在自我照顧上有多在行,卻忘記自己正身處的優勢是源自於其他人的努力。當我們理解自我照顧是一種個人責任時,我們往往忽略了照顧的政治面向。
曾有人呼籲發起照顧者的大罷工:集體地、公共地去反抗資本主義以各種形式吸納自我照顧這個概念並從中得益。西班牙行動組織無向漂流(Precarias a la Deriva)在「非常關懷(小心)的罷工(A Very Careful Strike)」文中發掘了照顧如何以各種形式被商品化,以及變得不被看見 — — 從市場中的性工作者、客戶服務工作者以至家庭中無償的情緒勞動。他們促使人們去想像將照顧從分層的社會剔除,取而代之,以其建立共同及促成革命。
但這樣的願景需要靠現在社會的邊緣群體共同實現。這將需要社會的大力支持,才可保障家庭照顧者、性工作者、秘書們在進行罷工時不會為自身招來可怕的後果。
因此與其主張自我照顧,我們應該重新定向及重新釐定「照顧」的意義。對某些人來說,這代表著承認我們一直以來如何從這不平衡的照顧分配中獲取好處,並把只專注我們自身的照顧,轉移至一種能使關係中所有持分者都可以得益的形式。你能休息是因為誰在工作?對一些人來說,這可以是指我們要更好地照顧自己、更好地認識我們這個權利 — — 沒有人應該為自己負起自我照顧的全部責任,那只是消費主義框架下(也正正是它所鼓吹的)物慾的自我。與其建立一個封閉的照顧社群,不如一起開拓一種廣闊的照顧形式,終結我們之間的分離,威脅現有的權力制度。
自我照顧的論述雖然被用以鞏固特權階級的權力和優勢,但批評的時候,也必不能反之令它成為武器,令本來已經難以尋求幫助的人添加困阻。換言之:前進,亦要謹慎守一步。
任何忽視照顧的重要性的抗爭都註定失敗。最勇武的集體抗爭亦是建基於滋養和關顧之上。但要重新奪回「照顧」的話語權不單是指要給自己多一點溫柔,彷似待辦清單上的另一個項目。它同時代表著要破除我們與統治者們之間的「和平協定」,收回所有只會不斷複製我們處境的照顧勞動,把它們用於顛覆與起義的目的上。
遠於自我保護
「『健康』的廣義下是一個文化現實,由政治、經濟、社會共同建構,亦連繫著特定的個人與集體意識。每一個世紀都勾劃著各自『健康』的正常標準。」 — — 米歇・傅柯
要推銷人們去接受一個規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包裝為對健康有益的行為。誰會拒絕健康這個概念?
但正如「自我」與「照顧」,健康不是一個獨立的概念。它本質上亦不等同善 — — 它僅僅是制度繼續運作的條件。你可以討論經濟是否健康,生態系統是否健康:兩者多數是對立的關係。這解釋了為何有些人會形容資本主義是一種癌症;又有一些人會指控全黑裝束的無政府主義者是癌症;兩者互相威脅對方的存在;一方發展代表危害著另一方的「健康」。
精神病學最明顯地展露了健康規範作為統治工具的特性。人們曾發明漫遊症及造反症以污名化逃跑的奴隸及反抗的人 ,今天的精神科醫生則把它命名為對立反抗症。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不止是一種精神科制度中的現象。
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不難想像為何我們會以生產力來量度健康。自我照顧與工作狂熱是一體兩面:照顧好自己以生產更多。這亦解釋了為何自我照顧的說法流行於非牟利的行業間,在要爭取到更多贊助費的壓力之下,機構就要模彷企業的模式,只是用著不同的術語。
若自我照顧只是為了減輕無止盡對生產力的追求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而非轉化成反抗生產論述的力量,它就只會是問題的其中一部分,而不是解決方案。要自我照顧成為一種反對資本主義的力量,它需要提出一個新的「健康」概念。
這尤其是複雜的,因為我們仍然在資本主義的運作範圍底下生存 — — 滲透著「生物權力」(biopower)的處境。人們認為在這個情況下,最簡單去維持健康的方法是在資本主義的比賽中勝過其他人。儘管這些比賽亦同樣地損害我們健康。「要是沒有其他藥可以吃,就吞掉讓你生病的那顆藥吧。」
要逃離這個惡性循環,我們就要從再複製某種「自我」轉移至另一種的生產。這要求一種全新的自我照顧的概念,一種超越性的而不是保守的 — — 允許人們理解自我是動態多變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不是要像西醫般把任何絲毫的變化擊走,而是找尋方法與之相處。在塔羅牌裡面,「死神」牌並不代表死亡,而是代表蛻變。
從資本主義及修正主義的立場來看,任何威脅到社會制度的東西都是不健康的。只要我們仍然處於舊有範式之內,那些「不健康」的東西就注定是可以帶領我們走出困境的指南針。而要破除及丟棄我們一直賴以生存的制度邏輯就必需要果斷。
這可能會解釋了有些人們一直傾向把反叛精神及自毀傾向相連起來,甚至龐克搖滾出現更早之前已經如此。 像佔領奧克蘭連線中,那兒所有的煙民 — — 有人愛稱他們作「黑肺群(Black Lung Bloc)」 — — 也的確是佔領運動中的肺癌前線!想要自我毀滅的力量可以把人導向物質沉迷或自殺,卻同時可以讓一個人奮勇冒險,成為改變世界的力量。我們可以以從自毀性的行為中找到線索,有一些是無限可能性的開端。我們需要發明新的語言去探索這個題目,以免我們現有的文字繼續挪用自我照顧的意義,徒添「疾病、自毀」與「健康、拼搏」兩者之間的偽二元對立。當我們說要打破制度中的某些邏輯時,我們不能單把自己說成是某個健康主體,在空無之中作出勇敢的決定。即便沒有自毀傾向,我們大多數人都經歷過疾病與障礙,讓我們從社會理想的「健康」中被剔除出來。就是這點迫使我們去面對健康和疾病兩者的關係,並與其產生的問題搏鬥。
當我們說及反抗資本主義的時候,我們也有把健康與生產力扣連、暗示著生病的人不可以有「貢獻」地參與嗎? 其實無需刻意把罹病人士打造成革命的主體(像Icarus Project一樣), 我們自己身上已經有不同程度的病痛,可讓我們能抽離並檢視資本社會對我們所設下的要求,足以擾亂那基於匱乏自我關顧及互相關顧而建成的自我價值與社會關係。與其將疾病和自毀病態化為為了提升效率而必需治好的失調,我們可以視自我照顧為傾聽自己的方法,帶出新的價值和可能性。
請想起維吉尼亞.吳爾芙、芙烈達.卡蘿、伏爾泰琳.克蕾,以及所有其他描繪了自己最私密地與疾病、傷痛和抑鬱抗鬥的女性,都展示了關懷與照顧不一定等於順從。那麼尼采呢?他罹病的身體僅屬靠他個人之力去超越的困阻,還是與他的洞察力、他的抗爭無法分離 — — 作為引領他發現已建構的知識以外的一個必要條件?若要以他整個生平來理解他的寫作,我們可能要想像他是一個坐在輪椅上衝向一列防暴警察的人,而不是胸口寫著S,在天空翱翔的超人。
你作為人類的脆弱不是一個需要感到歉意的錯誤,不需要緊張於「正確地」自我照顧、迫使自己返回社會齒輪的一部分。疾病、傷殘、及不事生產不是需要鏟除的反常狀態,它們是每個生命都會遇上的時刻,創造了我們走在一起的機遇。如果我們能認真地看待這些挑戰,開拓空間並專注其中,它們可以引領我們超越資本邏輯,建立一種照顧與解放不再是二分的生活方式。
三種視野
I. 忘掉安全
靜默的房間被訴說出的痛苦的重量壓得嘎吱作響。這個由兒時曾遭受性侵的男士組成的支援組,到了第三星期,我們不再進行籠統的自我介紹,而是深挖進創傷經驗中那些髒亂細節。
那一點都不光采漂亮。教科書上重覆說過的種種癥狀,成為這些男人生命中的真實經驗,他們要與憤怒、強烈衝動、性不安感、不信任感苦鬥,也受困於不可擺脫的羞恥感。坐在熒光燈下兩張金屬摺椅上的男人,其截然不同的生命歷程卻讓他們各自來到這個房間裡,他們希望從侵害經驗中療癒,這個嘗試為婚姻關係帶來不穩,也讓他們相連在今晚的聚會中。說到底,他們最害怕的是,若然將那些一直把生活截然劃分成不同領域,摒拒自己朋友和伴侶的保護情感之牆逐塊挖去,他們就會無法理解自己到底是誰,一直渴望又害怕的「破繭重生」也可能為他們的妻兒造成傷害。
邊呷著塑膠杯中的低因咖啡,另一人說著一直到晚年才能直面自己的創傷的故事;當他終於容許自己誠實,並告訴與他生活了四十年的妻子:其實一直沒有真正愛過她。一些人頭顱顫動了一下,卻沒有人能點頭認同;他們只是發出嘖嘖聲或是從喉嚨低吟哼聲。
我見到較年長的男人眼底攪動中的恐懼,他們的兒女正在近郊的家居等著他們。還有那些還未成家的年輕男子的不安。要踏進未知,進入那個以否認與自我防衛築成的馬賽克(其實等同於他們「自我」的身份)背後不知道為何的空間,讓他們恐懼。
和我一起帶領這個小組的發思人夥伴,渴望以鼓舞性的總結結束敘會,便機械式的笑著感謝各位的分享。然後,又展露出一個充滿希望的笑容說,他要每一個成員走進圈裡對各人說:「今週大家都要做的就是照顧好自己。」
房間內的目光躲向旁邊,大家的手翹在胸前。我尷尬得幾乎無法呼吸。
這些非牟利組織的「自我照顧」擁護者總是說著類似的話,每週如是,儼如儀式。但誰又可以投訴?我們當然要對怎讓放鬆、接地(grounded)、安慰自己去保持意覺,得力以繼續我們自己的療癒或支援別人療癒的嘗試。
但為甚麼這個問題今晚聽來卻完全不對勁?或者以這種虛假的正向思想來結束敘會,卻令成員坦露自己的痛苦變得很廉價;好像記得要冥想或是做運動,就真的可以減輕要回顧/疏理一生一直要隱藏兒時受虐/性侵的可怕經驗的痛苦。
當這些男人以遲疑的語調試著結束這次情感矛盾的分享,我發現事情比上述的情況更複雜。這關乎他們來到這裡的核心原因,他們是為了毀滅自我,以得拯救自己。那個當天坐在皮沙發上接受參加者訪問,說話時避開我的視線,訴說著那個繼兄弟或是家人如何粉碎了自己的童年生活的「我」,和十二星期後離開這個組織的「我」不可能會是同一個人,不然的話,這十二星期的經歷也只會是白費。正如他們細膩道來,自從被侵犯以後一直戴著面具般生活,因害怕過去的經歷被發現而抗拒親密關係,或是對身邊的人的欲望與需求,採取變色龍的態度,而賠上了自己的幸福。他們來到這裡不是為了照料那個囚禁他們與偽裝的「自我」,而是要它轉變。
這可以從兩種方式理解。一種觀點認為,在創傷的底層有一個眞正的自我,沒有被侵害及其後遺所損害──而只要他們能復原,這個埋藏的自我會重新導引他們,成為眞正的自己,眞正想成為的人。另一個版本,更令人害怕卻更接近他們描述的經驗:我們不會知道,假若他們的人生沒有被這般殘酷地打斷,可以怎樣地不同,而他們也無法知道,他們會在何時,或能不能在另一頭變成怎樣的一個人。工作,關係,身份,個性,沒有一樣是固定或穩定的。手被綁著,他們將寸步踏進深淵之中,因為可能會來臨的自由,或是至少擺脫一直以來的束綁而過不同的生活,感到畏高一樣暈眩。
所以當下一個男人講述他會帶他的狗穿過樹林遠足,或是要跟他的治療師匯報,我只能想像他要脫下面具和偽裝,滑落懸崖撞在石頭上、要急速跌進未知那種讓人癱瘓的恐懼。又或是一個緊緊纏繞的繩球,跌撞之間散開來,裡面卻甚麼都沒有──那痛苦地繃緊的線終於鬆開了,卻發現它一直繞在一個中空的內裡。我迷失在類似的思緒中,差點沒發現我的發思人夥伴正期待的看著我。每個人都已經發言。
我笑著開了個關於自己的玩笑,希望賺些時間想想可以說些甚麼開心一點和自我肯定的話,但時間一秒一秒過去,拖延變成令人不安的靜默,即試我願意嘗試,也實在想不出一句「我會怎樣在這次分享之後如何減壓……」那種鼓勵人的客套話。
我的腦海反而充斥著報復的幻想,無能的憤怒、哀傷和羞恥感噬咬著我。更重要的是對這種意識形態的蔑視──即使那是出於多好的本意;同樣叫我蔑視的,是那些要求我們平復的嘗試、將我們為存活而作的絕望奮鬥,重新演述,變成再次肯定這些梱綁的自我和創造這些枷鎖的世界。我的舌頭打結,我的心在跳。我開口說:
「我… 這個星期我會寫作,寫作能幫我整理自己的感覺和想法。」
他鬆一口氣的微笑,返回小組裡,跟大家道晚安前,說著「照顧自己的重要性」等等空泛的話。椅子刮在地板,手堅定的握過,隨又插進褲袋裡,男人們躬起肩膀陸續步出,走進寒冷的十一月夜裡,走進瀕臨災難的世界之中。
II 走出舒適
我們圍圈聚在一起,參加一個表達對自然環境哀悼的儀式。組織者帶來背景分殊的參加者;我見到一個頭髮剷掉,一半耳陲塞著耳擴的女生幫一個不能坐在地上、長一頭灰長髮的女人找椅子。我的斜對面坐著一個生意人,他最近促請律師提告那個我最近親吻過的人,予以可判刑的重罪。我為此感覺不安,但如果「社群」就是由鄰近而互相影響的人組成,我們的相遇就很合乎這個定義。
我們逐個加入圓圈中,圓圈分成四等份,放有不同的象徵物件。我們把乾樹葉擦在我們哭泣的臉上;憤怒地向天空揮動樹枝;我們捧著碗凝視我們混亂思想中的空洞;石頭與那些讓我們動彈不得的恐懼沉在我們手中,儀式化的癱瘓是為了讓我們從恐懼中釋放。當我們說話,故事便能會流淌:沾上毒癮的兒童、被關在獄中的朋友、即棄的產品、被破壞的山嶺。在我們共同與獨有的困境中,我們是彼此的見証人。
這是健康的動物面對牠們的憂傷與壓力的方式。牠們會聚在一起,也會互相照應。大象會為死去的同伴,發出聲音並以特定的動作進行儀式。靈長類動物都喜歡互相整理毛髮,舒緩神經且藉此建立自願的社會連結。就算在冰冷的實驗室裡,老鼠也會一次又一次的從籠裡救出同伴。
在我們的文化中,要做健康的哺乳類動物卻不容易。像我們的哺乳類親戚一樣,我們已演化至會因為樹枝斷裂的聲音或是忽然經過的陰影而驚動,當危機過去又會再次鬆弛下來。但我們卻生活在一個就算是美好的一天也是神經系統難以應付的環境:我們在通風不良、牆壁平坦而充滿尖角,予人無可逃避的禁閉感覺的封閉空間中工作、學習和社交。我們的大腦新皮層(neocortical brains)被不止息的各種嘈雜聲音和影象轟炸,早已刺激過度,新聞則告訴我們無止盡的種種威脅:校園槍擊、工廠大火、壓裂採油法、約會迷姦藥物…… 經驗此種種同時,我們被要求保持冷靜、紀律而且保持生產力。
我們的神經系統渴望變動──追求一波又一波令人好奇與感興趣的事物隨後感到充實,警覺然後放鬆,基於共同的感觀與情緒經驗而與他人發展聯繫。當這些節奏被擾亂,我們的大腦和神經系統便進入不同的失能狀態:過度警剔或是停擺,憂鬱或憤怒。為了逃避這些狀態,人們沾染了各種癮習,因為這些癮習模擬了需要與本能被滿足的感覺;譬如強迫性購物對應我們搜尋的本能,互聯網色情對應我們的性欲,派對藥物則對應狂喜的精神狀態。我們生活其中的體制,一方面提供這些讓人沉溺的事物,同時又羞辱那些放縱的人;然而我們各種追求與自然狀態所得的心理效果,卻不能由這些替代品模仿,大腦與身體因此變成癱瘓或是停留在過度刺激的狀態。
我生於一個甫出生就被視為附有「原罪」的家庭裡。靈魂的生命被身體所剝奪,這具身體的控制和被支配就如聖寵同樣重要。當家父去世,我可憐的母親就得從世俗生活與其可能發生的永恆詛咒中,拯救家裡的三個少年和一個小孩。在她的經驗裡,也只有一種管教方式,當她只能獨自面對養育一群骨肉的責任,她採取古老的教條:「放下棍棒就會寵壞孩子」(spare the rod, spoil the child)。我因為各種自身本能反應而被打,譬如對教會的老人微笑、吞下質感奇怪的食物後嗆吐…也不要說只是打翻了牛奶等等小意外。
長大成人的我現在照料自己,感覺就像可以知道「甚麼是對自己好」,並且可以選擇的自由與福份。另一方面,自從孩童時就學會,別人給予我的照顧總附帶著條件,如牽制的繩子,甚至像監獄般裝了倒勾的網和電網,與人親近而顯露軟弱或會令我感到不安,甚至危險。有時我無法回應、甚至不能接受別人的善意。對我來說,最簡單和熟悉的反而是孤獨。
就像許多倖存者一樣,我可以孤立自己同時參演「自我照顧」的刻板形像。當我跑步、練瑜伽,為那些關於接納自我的書籍撰寫好評,或是把我的情緒導向一些藝術計劃,或是在博客文章裡坦陳自我,那些時候我可以顯得很勇敢甚至進步,這種形式的「自我照顧」與其說是解放,卻更像是單獨囚禁。
有時,我眞正需要的是有人能幫忙買外賣到我家,讓我吃飯的時候有人陪伴,等到我在沙發上睡著,送我上床、幫我蓋好被。有時這不需要我提出請求,也有時我得鼓起勇氣向人求助,告訴別人我需要人跟我說話,或是讓我哭,總之就是不用獨自面對。有些時候,能夠放下自我照顧的堅持(讓人照顧自己),才是最激進的自我照顧方式。
我當然相信情緒的自我管理,我們需要那些不帶攻擊性而能平復激動情緒的技巧,以及能自主而快樂地去遊歷、工作、探索未知。但這不等於我們需要孤獨地管理自己的情緒,也不等於我們應該如此。
當我開始研究創傷的時候,我學到關於戰鬥或逃跑反應 (fight or flight) ,被迫到牆角的動物,都會逃跑或反擊,視乎當時哪種是最好的策略。後來我認識到僵直狀態(freeze),在危險解除之前裝死的本能,還有當危險看來無可化解的時候,一直停滯在這種僵直狀態的可能。這是很多受苦於創傷後壓力失調的人為甚麼最初都曾被診斷為抑鬱症的原因:他們停留在那個僵直的回應狀態。
最近我也學到,當社會參與失效,我們就只能逃跑、攻擊或是裝死。我們處於壓力或是受威脅的時候,最先的本能反應是團結或是尋找別人以求安慰,如果成功,我們的恐慌反應就會退卻,而我們就能回復到諸如遊玩和創造的能力。既然我們的神經系統對於他人在場與否有如此大的反應,很明顯「自我照顧」和「互相照顧」是不能分割的。
當我們明白,我們的種種壓力和創傷是共同的困境而非個人的病理,把互相照顧看成優先的重要性就更清晰了。作為人類,我們正活在一個導致無論情緒和生理狀態都失去連貫性的環境之中,即使我們不能立刻根除這個監禁著我們的體制,但若我們能辨清我們的奮鬥和問題解決方法都不僅屬個人的,機會便會大大提高。若我們能找到更多坦誠與人共同行動的方法,無論是傷心或是興奮,我們都會變得更強壯與堅韌──個人和集體亦然。
III. 毀掉你的名聲
多年以來,我的自我照顧方式都是錯的。
我從多年來各種陳贅冗大對話中,學會了這些字眼。例如找尋「安全空間」,似乎是要解決種種複雜問題最容易的第一步。但是「安全」和「照顧」這些概念只開啟了其內在的空洞。有多少人曾在任何環境裡面,真正覺得安全?有多少人打從骨子裡感受過照顧是甚麼感覺的?
在二零零八年的夏天,車輛的引擎和混凝土路面疊加著費城的炎熱,在騰騰的熱氣之中,我躺在共住房屋三樓的一個小房間,卻沒流著一滴汗。我床邊的櫃子上佈滿喝光了的鋁箔包裝椰子水和一包包綠色的電解質沖劑,還有一堆朋友給我買來的東西。在靜默無聲的海浪之間,一些想法在我的腦海漸漸浮現。我知道這是一個內省的時刻;我一直以來駕馭自己身體的方法需要一些改變。我被留院觀察一夜後,醫生著我回家,除了開一些止吐藥就沒說甚麼。這已經是十天前的事情,我的消化系統依然在罷工。我虛弱得無法獨自下樓到廁所。我定時就會把食物塞往喉嚨,結果是災難性的。痛楚如浪般擊向我的頭和腸道,休息幾乎是不可能的。
會淪落得如此地步就似是標示著我個人的失敗。致病的原因是個謎題。沒有診斷結果,沒有一個敵人可責怪,我無法阻止自己去想一切根源都來自我個人的缺陷。
關於我對自己的理解,有一點總是不變的:我有毛病,而我需要修正它。只有這樣想我才可以正常地生活:去發展技能,去幫助他人,更重要的是──去變得值得被愛。我有責任糾正自己,不讓自己勞累到別人。這個想法僭伏在我的意識,我自己亦難以察覺,卻形成了我的身分認同和我去照顧自己的方法。我把「如果你想照顧別人,就應先照顧自己」這句說話理解成「為了可以照顧別人──那才是你的主要工作,你要照顧自己。」,並內化了這種命令。
我花了很多年去嘗試修理好自己。我的方法看起來很像是自我照顧:把不好的食物從我的餐單剔除、做冥想,瑜伽、定期運動、接受心理治療、閱讀關於神經心理學及創傷的書藉。同時,我努力嘗試跟上朋友的腳步。我時常妒忌他們的正向能量及耐力。當我的身體僅在一個小時後就開始疲倦,我強迫自己忘記痛苦,繼續工作。當我找不到不會讓我致敏的食物時,我就甚麼都不吃。我硬拖自己到瑜伽班,強迫自己要做得到讓我快要受傷的瑜伽姿勢,因為我需要相信自己正在做些甚麼去對抗自己身上的毛病。當病情復發又再一次使我的身體垮掉時,我強迫自己休息 ──儘管我害怕獨處。通常休息是指把自己關在房間然後狂看蠢電影,直至自己麻木。任何可以讓我避開絕望及面對自己的支離破碎的事情我都會做。
我已嘗試過所有我可以照顧自己的方法。出院回家後躺在床上,這戲劇性的失敗也確實是尷尬。於是我嘗試與身體宣佈休戰。我問身體,你需要些甚麼來回復原來的運行呢?我已準備好去妥協。但它的回應卻讓我畏縮,就彷似有人把一個正放聲嚎哭的陌生嬰兒突然放在我手上,然後叫我要視如己出地去愛及撫養他成長。
在這個社會,我們所培育的個人人格都與生產能力最大化相關。我們學習去控制自己的慾望和限制自己的需要;能夠自供自足和表現忍耐是為人稱道的特質。當一個好的員工、專心、控制自己的情緒、超越自己、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窮盡氣力去平衡這些原則為人帶來勞累的後果,市場就為我們這些消費者提供自我放縱的空間。獎勵自己、奢華、縱容自己的熱情、清空壓力。在社運文化裡面人們也時常在這「自我控制 — 自我放縱」中來回,我們懷有資本主義式的工作道德,同時質疑資本主義的物質舒適。當我們說及自我照顧時就往往是在其中一端。努力鍛練,或者去做按摩。禁食來清空毒素,或者休息一天來獎勵自己。用治療去處理你的糟糕事,又或者浸個泡泡浴。我們盡了所能去照顧自己,我們依循資本制度內老生常談的方法 ──那些總把我們重新帶回起點的方法。
如同鉛、砒霜、水銀以及其他工業毒素殘餘我們體內,我們心理上也吸收了我們文化中的價值及暴力。我們大可試圖從這些毒素中療癒,而不逃離或嘗試改變持續傷害我們的處境,但這將是一生的徒勞無功。絕對的健康從來是難以達至的狀態,可以變成一種執迷。基於自我控制的自我照顧就像免疫系統:我們看守著我們的界線,奮力維持界內的純淨。當我們在自身找到不想要的特質,就對其作出威脅及發動攻擊。自我放縱的方法如同鴉片一樣,減輕我們的痛楚及舒緩病癥。第一種方法基於一個嚴謹地分別何為自我及何為他者,而第二種則要我們判斷要放棄的哪一部分以保存自我。兩者都使我們永無止境地追逐。
也有第三種方法。是種類似鍊金術及消化系統運作的方法──緩慢地將物質混和及將其轉化至另一物質,這過程需要著個人的耐性及流動性。當你的自我無法僅以一個形式:一種年齡、一種尺碼、一種心情、一種體能去承載,你可以試試與那些看似有害的壞物質共處,慢慢地分解再重組它們,直至它們成為全新的──你。這個方法與普遍方法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在實驗結束之前,你都不會知道你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
我康復的轉捩點來自於我停止嘗試修理自己。多年無間斷的自我照顧化為僅僅是對健康的幻想:渴望成為一個能靠很少燃料就可以發動,而且不會被受傷或悲痛拖慢──一個能夠不懈地工作的人。總而言之,就是一個從不需要被照顧或關懷的人。儘管我一方面在寫作反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只要我還是以這些正常生產力的標準來斷定自己的價值,我就依然與市場的道德觀同出一轍。
當我與我的身體宣告休戰的時候,身體給我最令人擔憂的信息就是我無法以理性解決我生病的謎題。沒有一個程式、程序、或是萬能的解決方法。這不是工會的罷工,而是全體的起義。而我的身體只有一個訴求:放棄吧。你一定會喜歡這樣,正正就是這樣。這個不完美,毀壞了的身體可能永遠也不會痊癒。你乏味的腹痛。你的恐懼與孤獨。隨心跳的幾下警號後我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處境。這個身體有甚麼好愛的?即使我問出了問題,悲傷依然模糊了我的視野邊界。
照顧一直都是一個抽象的空白,似是另一種工作形式的代用詞:就像工場裡的農夫怎樣照顧籠內的雞。現在似乎已經被黑暗的光華充滿,像一個玻璃的容器內裡正沸騰著一些危險的物質。它不是瑜伽老師答應我會從訓練核心肌群找到的內在寧靜。照顧是恆變和不固定的;高度密集的個人化,卻又同時重新連結內在。我肌肉與內臟灼熱的疼痛沒有減褪,但它們開始分明──變回構成和音的一個個音符。而對抗我不合作的身體所累積的沮喪沒有完全消失,它甚至加劇,變成憤怒,但是一種向外的憤怒,保護自己的憤怒。
我經歷了人生最大的轉變。我停止站在敵人的那一方。

